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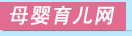
你可以用手机、ipad随时随地看《活着》
不分平台,不限时间。订阅《活着》,你可以:
【微信】“扫一扫”左侧二维码,或搜微信号ihuozhe;
【腾讯新闻】手机客户端 订阅管理中搜“活着”;
【ZAKER】手机客户端 搜“腾讯新闻原创精品”;
【网易云阅读】手机、ipad客户端 搜“腾讯影像力”。
七台河是省一个不足一百万人口的小城市,市中心叫“山上”,小到开着车不消十分钟就能转一圈,小到随便在哪家餐厅吃饭都有可能遇到熟人。大概这几年出了几个速滑冠军和几次较大型的矿难,便因此有了些名气。七台河在过去不过是个不知名的小农村,除了日本人曾经来拓荒,光顾更多的大概是了。后来这里因为发现了煤炭,在1970年时变成了地级市,辖着三区一县。由于处于和之间,交通极为不便,基本没有什么能直达的火车,也就因为煤炭,勉勉强强从当年日本人修的牡佳铁分个叉修进来一条铁,否则连个弯都懒得拐一下。
我出生在这里,但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到底哪条河是七台河,抑或到底有没有这条河。
我父亲在1970年从带着奶奶来到了七台河,谋得了下井采煤的工作后,在一个当时还能称为青山绿水的地方盖了几间土房,有干净清冽的井水喝,有一个大大的院子可栽种蔬菜,院子外的树林有蘑菇和榛子可采摘,甚至还有狼会偶尔光顾。我每天可以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发呆,等到父亲从矿里下班后带来面包,拿出来分给小伙伴们吃。那时候,邻居寥寥可数,当年来东的人就已经算是本地土著了。
父母的朋友大多来自煤矿,那时工人和干部的差别不大,反正升了井口都统称为“煤黑子”,我的学龄前教育都来自父亲矿里发的那些安全生产的小。那时煤矿安全条件恶劣,几乎每一个在井下工作十年以上的工人都有从鬼门关捡条命的恐怖经历,父亲我将来宁可要饭也不能下井工作。
到了80年代,父亲在前院又盖了几间砖房,我在此之后完成了几大重要的人生大事:上学、工作、娶妻、生子。七台河的人口多起来以后,虽然矿区依然乌烟瘴气,但也逐渐有了些沥青铺砌的街道,山上有了城市的面貌,市场开始热闹,治安开始混乱,开始污染,开始分化。我家院子外铺设了一条通往洗煤厂的铁,邻居越来越多,井水开始浑浊,诺大个森林最后被砍剩个小小的桃山公园。
我顺着父母为我设计好的人生道,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矿办中学老老实实地当了几年老师,我紧巴巴地数着每月发的二百多块钱工资犯愁,矿务局却经常几个月都开不出工资来。煤炭经济在那个时候开始走下坡,虽然后期有过几年的回升,并造就了诸多暴富的煤老板,但煤炭行业的颓势注定不可逆转。我看不到希望,就辞职去了,随后接走了父母和儿子,而这一走就是十年,没啥牵挂,连念想都少有过。
其实这十年,并非一次未回,但每次都不过是因事来去匆匆,都不愿作片刻停留。七台河城市格局的变化使我曾经的二十多年生活经验作古,变化到我经常迷,这里多了各种冒着的化工厂、焦化厂和电厂,有了很多和其他小城市一样更宽阔但又很拥堵的马,有了更喧闹繁华的商业区,有了豪华气派的办公楼,有了各种起着洋名的高层住宅小区,有了肯德基、必胜客,口新设立的红绿灯多少改变了七台河人出行的许多习惯。
这种变化一开始就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新奇,当我拿着相机把故乡当做项目来拍摄时,我发觉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这个城市。我想拍到每一处细节,我甚至想为这个小城市建立一份图片档案,我躲在相机后边,地观察和揣摩着这个城市,像一个外人,远远地、小心翼翼地拍摄,故乡此时也仅仅是照片,是不动声色的异乡景观。但随着返乡的次数和时间的增加,当故事和新闻不断被和,我便能轻易地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地方找到线索,七台河又被自己慢慢熟悉并适应,我逐渐陷入其中,就像被不断延伸的大网包围住无法梳理但又不想,甚至曾想过有没有留下不走的可能。
后来,返乡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父母惦记朋友们的近况,想看到朋友们的照片,我便就尽量替他们去拜访。他们那一代人都已退休,而且大多都已去世,活着的、生活情况稍好一点的,很多搬去了外地,留在老家大多是父母的穷朋友们。他们年轻时带着力气和来到这里,亲历着这个城市的兴起和繁荣,把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建设成后来中国最好的焦炭,他们把一生及他们下几代的希望都留在了这座煤城。当他们逐渐老去的时候,他们挖空的不仅仅是煤炭,他们似乎也把这座城市的未来挖空,一代人的生命和一座城市的兴衰就这样高度同步着。
随着煤矿的开采作业,造成的采空区,的建筑沦为危房,那里大量的居民将被拆迁至北边新建的巨大社区内,市就必须斥巨资为大势已去的煤矿副作用买单。桃山矿、新兴矿现如今已被拆解得满目疮痍,我上学时的教室,只剩下几面残垣破壁和一个表情呆滞的打更老头留守在那里,我每天上班过的喧嚣热闹的井口因荒废长满野草,儿时经常去烤马铃薯的矸石山被削平拉走,铺基盖新房,街道和胡同随着房子一起消失了坐标,除了垃圾就是瓦砾。那些我一个个熟悉的地方变得面目全非,虽然与此关联的回忆谈不上多么难以磨灭,但也因景物的消失会变得,连触景生情的机会都没给留下来。
或许是我因与故乡十年的记忆断层才如此感慨唏嘘,年轻一代和更年轻的一代似乎对此毫无眷恋,他们从四面八方的矿区搬迁至山上舒适的楼房里,开始享受着这方圆几里的城市现代化生活。矿区的学校生源锐减,桃山矿原有的九个中小学现在只剩下两个,反观山上的学校却人满为患,有的一个班级就有80多人。年近不惑无欲无求的70后家长们,孩子求学之才是他们走出这里的重要寄托,他们看得到问题,感受得到危机,但被父辈和单位招安而习惯的思维方式使他们集体选择,茫然,苟且满足,因为,他们早盘算着这个已现疲态的城市至少还有30年可供支撑消化的脂肪,所以各家餐厅里的酸菜大鹅龟锅肉串的货比三家才是最现实最快乐的话题。
人无法选择出生,就无法选择故乡。据说老一辈的朝鲜族人在死后会将骨灰洒进松花江,随着江水漂流到遥远的朝鲜海。父亲虽在七台河生活了30年,但在生活的十年中,让他魂牵梦绕的老家却是他出生地——。儿子三岁前都在七台河,现如今操一口流利话的他早已没有那时候的一丁点儿的记忆。对他来说,七台河与任何一个北方小城无异,在东北滑雪的乐趣远大于他对故乡的认同,即便是在他出生时生活的矮炕上都也没找到故乡的归属感。而我无论落身何处,身份证永远都是2309开头的号码。多年在外飘荡,让我失掉了在这片土壤里留存的能力。如果故乡是原点,我将像洒在河里的骨灰顺流而下,再也回不了头。只是这座城市,迟早会变化到我无法再相认,所以我庆幸自己还是拍到了我眼中的七台河,如果将来不得不按图索骥来回忆故乡,这便是一份可共享的图片。
>
点击进入网络书店查看、购买《影像中的国》